那年七歲,毫無預兆下,父親突然將整塊玻璃往肥仔丟過去,導致他頭破血流;自此,父親被判不得再接觸兒子,他隨後分別輪流到寄宿學校及跟太婆、姑姐等不同親戚生活,像是丟來弄去的包袱。
直到中二那年,房屋署查到太婆家沒有肥仔的公屋戶籍,他要跟父親及爺爺同住。相隔數年,他沒想過再次回到地獄。「因為親戚都怕了照顧我,沒人照顧就要跟爸爸住。」然而,肥仔再度被父親虐打,加上學業成績倒退,他決定輟學工作,找了一份包住宿的茶餐廳學徒維生,開始過着沒有根的生活。「離家是很開心,算是離開了地獄。因為不能回家,找的工作一定要有地方住。茶餐廳安排膳食、有地方睡覺,已經解決了人生最大的問題,不會說什麼興趣。」肥仔瞇着眼笑。

自輕微中風後,肥仔的心跳比常人緩慢,除了不能工作,還要定期服食多種藥物。
肥仔憶起,那時廚房工作沒有休息時間,晚上收12點,明早6點就要起床開工。他回到宿舍就倒頭大睡,睜開眼又是十七、十八小時的工作。生活即使被工作佔據,肥仔仍選擇22歲時跟餐廳的女同事結婚,為的只是一個申請居屋的機會。「那時候都想有個家,有個穩定的家,所以就結婚抽居屋。」兒時因為父親而過着顛沛流離的生活,長大後就想結束以宿舍為家的日子。然而,肥仔卻說不出當時對家庭生活有什麼憧憬。他單純希望有個屬於自己的地方,而結婚恍似是一個手段。
二人的婚姻維持了僅僅兩年,就宣告離婚。「我結婚是為了抽居屋,當時她(太太)想生小朋友維繫這段關係,但我堅決反對。因為我經歷過,當父母不能提供一個好的環境讓小朋友成長,不如不生。」
失婚之後,肥仔的事業則愈發順利。七八十年代是以汗水和勞力換取金錢的時代,肥仔於十年間由廚房學師逐漸爬升為判頭,即餐廳需要幫工時,就會聯絡他找人。那年,他只是二十出頭,當時只要撥出一兩個電話,隔天就找到四、五十人來幫忙。「做判頭人工每月有三萬幾,那時候我有人、有錢、有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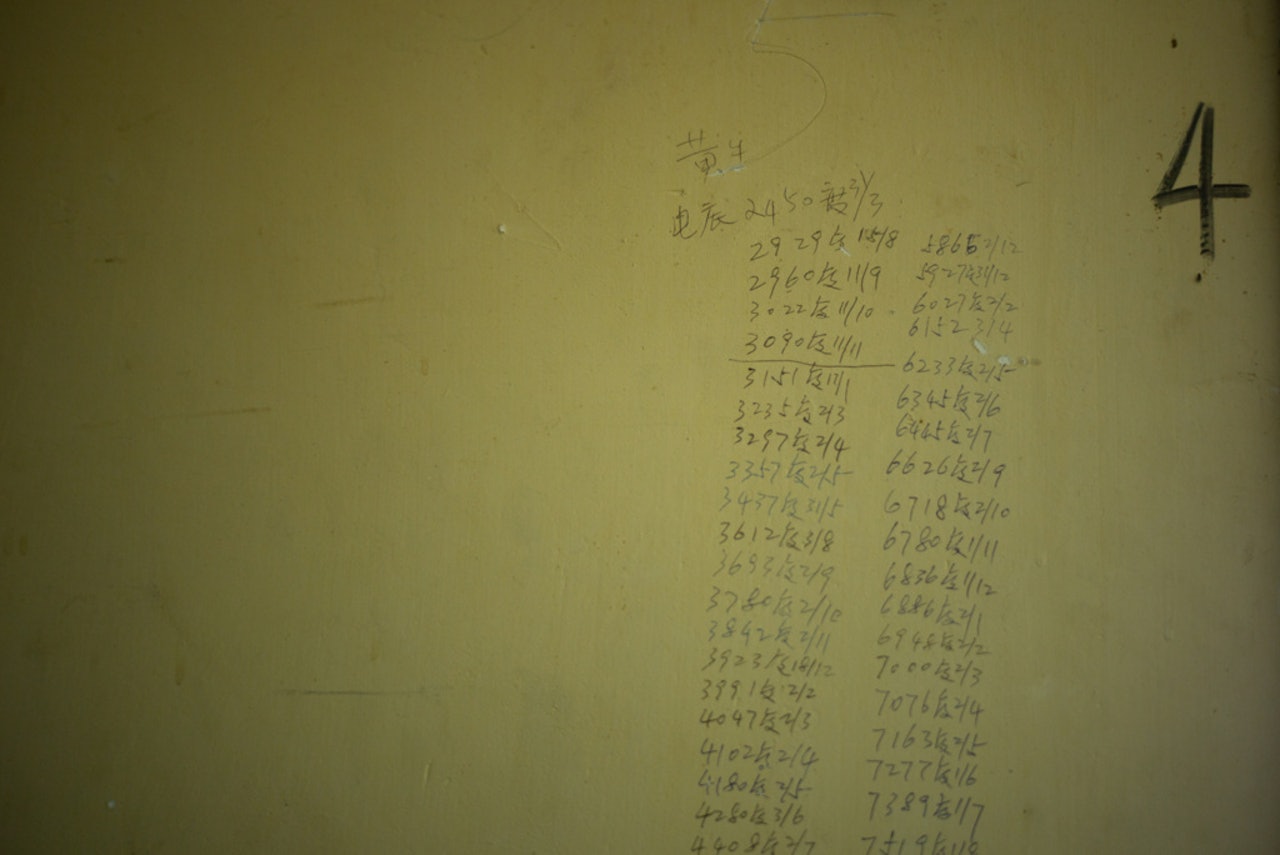
「當時她(太太)想生小朋友維繫這段關係,但我堅決反對。因為我經歷過,當父母不能提供一個好的環境讓小朋友成長,不如不生。」風光過後孑然一身。
1990年代,普通廚房師傅的工資約一萬多元,肥仔靠着人脈和經驗,賺取比其他人多逾兩倍的薪金。事業得意,肥仔兒時被虐打的陰影漸失,滿臉意氣風發;加上當時管理的壓力沉重也教他十分煩躁。「說話都說得大聲些。自我膨脹得好厲害,脾氣亦較為暴躁。當時認為你說話不順意就罵,不想討論。」
那個年頭做飲食業賺得多也花得多,即使肥仔月入逾三萬也沒有多餘的儲蓄。「廚房大佬都喜歡上大陸玩,聊天都要在夜總會,一星期一至兩晚也花掉了數千元。」
風光的時間僅得短短三年,肥仔因為跟老闆意見不合而失去判頭一職,失業後也曾嘗試跟朋友合資開食肆,後來因為經營不善而相繼結業。當年一呼百應的風光不復再,這教他醒覺當初與朋友的關係是如此淡薄。「原來當時的『朋友』是看我老闆做人,覺得我靠着那個老闆搵到食,就靠過來;所謂的朋友,一切都是建立於金錢,沒有錢,就什麼都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