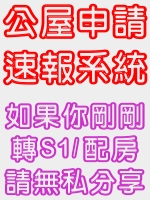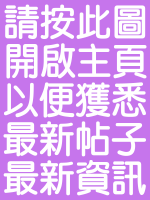|
心情動態:
來自非公營房屋 |
青年「破繭而出」與預防「下流老人」
《小偷家族》講述生活在東京底層一老三大兩小六人在沒有血緣關係下,共同生活的貧困紀事。(圖片摘自網路) 在台頗賣座的《小偷家族》(萬引き家族),代表日本在坎城影展榮獲睽違廿一的「金棕櫚獎」最佳影片,由枝裕和導演,故事講述生活在東京底層一老三大兩小六人在沒有血緣關係下,共同生活的貧困紀事,發人深省。電影呼應了日本社會的「八〇五〇現象」,高齡八〇歲的父母,還要扶養五十多歲宅在家的兒女。 電影描述高樓旁一棟破舊小平房的柴田一家五口,靠著父母兩人打零工與婆婆的老人年金度日,在生活艱困下,平時常到商店偷竊日常所需,在一次行竊後,父子兩人發現一位餓肚子的小女孩,將她帶回家中展開一家六口的生活。 日本的老人在退休後除靠退休金過日子外,還透過政府社會福利政策的「老人年金」生活,只要是日本國民有按時繳稅,無論是否曾經工作,都可以享受這項福利。 由於曾經為日本企業服務的員工在退休後,都是一次性地支領「定年金」,所以沒有按月發給的退休金,「老人年金」成為生活開銷的基本支持。 在日本經濟進入上世紀九〇年代後出現的「消失廿年」,景氣持續低迷,且在二次戰後第三波嬰兒潮投入就業市場下,眾多五、六十歲的日本男性在過去十來年裡相繼失業,在東京成為社會中底層的「瓦愣族」,意即露宿街頭以瓦愣紙箱築床而居的「日雇勞動者」或「流浪漢」,亦謂「下流老人」——又窮又孤單的老人。 日雇勞動者,指每天都在不同的地方做零工按日計酬者,日語稱「無定職」,其勞動環境惡劣,無固定收入,若有收入亦很低。通常由勞務派遣公司分派工作,且不負擔社會福利與保險等成本,無法有工傷保險等勞動保障。為能享有醫療保險,向政府申請「低收入生活保護費」,取得稅務免除的待遇。 流浪漢多為中老年男性,在收入低微下無法負擔生活費,羞恥地不辭而別家庭露宿街頭。猶如蜂巢糧食不足遭遇溫飽危機,老工蜂離群索居,將食物遺留給年富力壯的年輕工蜂,選擇以「孤獨死」面對未來。 另外還有「啃老族」分享老人年金,一家高齡者和子女孫輩,仰賴微薄的退休金共同過活。甚至在領有老人年金的長者過世後並未通報政府,悄然處理長輩屍體,繼續冒領老人年金,此等現象在七年前後成為了日本社會的熱議話題。這正是導演枝裕和無意間看到一則家人隱瞞老父去世事實,非法詐領老人年金的社會事件報導有感而發的創作。 日本總務省二〇一六年對勞動力的調查發現,日本卅五至五九歲的中年啃老族有一二三萬人,是一五至卅四歲青年啃老族的二.二倍。中年啃老族從青年時即未有過多的工作經驗,步入中年更難求職。 和日本類似,南韓有「袋鼠族」、日本「寄居族」和台灣「靠爸族」或「米蟲」,而「尼特族」在土耳其有三成、義大利廿七%、希臘廿五%、西班牙廿三%,澳洲更有超過六成的青年人寧可賴在父母家成為「啃老族」。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去年發布「社會掃描」報告,二〇〇七年至二〇一四年,美國的年輕人,和父母合住的比例為六六.六%。中國大陸對「繭居族」有精彩的形容:「一直無業,二老啃光,三餐飽食,四肢無力,五官端正,六親不認,七分任性,八方逍遙,九(久)坐不動,十分無用。」青年如何「破繭而出」找出路也是個國安和經濟問題。 
|
|
2004-10
|
|
|
心情動態:
來自非公營房屋 |
|
|
2004-10
|
|
|
心情動態:
來自非公營房屋 |
當安置機構接連停業,誰幫司法少年撐一把傘?
 在少觀所接受觀護的非行少年。 在少觀所接受觀護的非行少年。[size=1.22222] 當步入人生風暴的非行少年無家可回,收容他們的安置機構,像是為他們撐一把傘,陪他們走一段。但近一年半來,台南7所兒少安置及教養機構,有3所接連停業;這些年,全台也不乏安置機構縮減收容名額和對司法少年挑案的例子。 當機構自身在風雨中左支右絀、自身難保,這把傘,還有多少力氣再撐下去? 2017年1月開始,台南7所兒少安置及教養機構,有3所接連停業。停業的蔣揚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附設鹿野苑關懷之家、基督長老教會加利利宣教中心附設台南市私立希望之家,是國內少數願意收容司法少年 的機構之一,鹿野苑更是極少數收容女少年的機構。 提及停業原因,3所機構一致表示「找不到人」。多數人會聯想到薪資過低,但網路上還有鹿野苑的徵才公告,社工師月薪49K,生活輔導員月薪39K,其實不差。 台南市政府社會局婦女及兒童少年福利科長郭元媛表示,機構反映,《勞基法》修法後,生輔員從以往的彈性排班轉為三班制輪班,墊高營運成本;且就算有資金,兩間機構都位於偏鄉山區,交通不便,人才長期難尋,讓主事者決定收手。加利利將轉型社區與弱勢家庭服務,鹿野苑仍在思考後路。 2017年3月,南投專收司法少年的「Z機構」爆發超收、院內性侵、暴力管教,遭到罰鍰停業,8名相關公務員和少保官,因不知機構超收及未通報性侵案件等由,在今年7月遭到彈劾。安置工作第一線人員認為,Z機構事件,反映出社政、司法兩大體系對於安置輔導處分法律位階不清、長期缺乏協調聯繫等問題,若根本問題未解,彈劾恐造成「調保官不敢建議安置、機構不敢接司法少年」,原就不好找安置處所的司法少年,更無處可去。 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家的價值無法替代,機構即便努力營造家的樣貌,仍無法取而代之。加上機構環境相對封閉、疏忽與虐待事件未曾間斷,「去機構化、加強前端問題預防」,已是國際對於兒少安置的思考風向。 但在政府拿出對應配套前,安置機構對部分孩子來說,仍是脫離失能家庭,暫時喘口氣的機會。 長期投入司法安置工作的台東海山扶兒家園主任林劭宇認為,彈劾案後,機構對於司法少年的態度勢必更緊縮。「Z機構受到不少批評,但我們得自問,Z機構不收,我們誰敢收?可惜的是,協助高難度孩子的機構沒掌聲,出事了政府卻欠缺輔導,只會讓機構愈來愈挑案。」 少人、缺錢、憂標籤 早在彈劾事件引發寒蟬效應前,以收容行政體系社政安置為主的機構,基於人力、經營成本、形象、評鑑等考量,對於是否接受司法少年,態度就已相當保守。 「大家覺得你照顧非行少年 很有意義,但別跟我小孩同班。」多間安置機構指出,其實社政安置兒少同時有犯罪行為,並不罕見,照顧難度絕不亞於司法安置的非行少年。但接受司法安置的機構,就被貼上「這裡有壞小孩」的標籤,導致鄰避效應,也有多所機構的孩子曾被當地學校拒絕入學。 |
|
2004-10
|
|
|
心情動態:
來自非公營房屋 |
機構內部,不僅有「壞孩子會帶壞我家小孩」的照顧隱憂,且每收一個司法少年,就會為已飽受「缺人」與「缺錢」困境的機構,再加一重壓力。
被安置到機構的孩子,絕大多數帶著過往人生的傷口,這些創痛往往反映在外顯行為上。背負家庭與犯罪雙重問題,需更多人力與更強的心理素質的照顧,才能因應動輒鬥毆、爆粗口的司法少年。 根據法規,每照顧4位司法兒少,需配置1位生輔員,是社政安置每6人配置1人的1.5倍。弔詭的是,規定中沒有闡明這是「隨時人力比」,還是「總額人力比」。 南投陳綢兒少家園主任徐瑜舉例:「單以機構生輔員來說,需輪3班,工時8小時。假設這間機構收20個司法安置少年,以總額人力比來說,要請5名生輔員。但是生輔員要休假、受訓,孩子半夜可能要外出看病,以隨時人力比來說,得請15人,才能維持現場有1個人照看4位孩子。」  南投陳綢兒少家園主任徐瑜。(攝影/吳逸驊) 「不如你給我標配,我自己擴充成全配」 對被安置的兒少而言,機構被定位為「替代性家庭」,但這個家庭得顧及整體營運,並得為生活輔導員等「替代父母」們支薪,就算是非營利性質,也絕非功德事業。 與人力比環環相扣的,是機構的人力成本。若生輔員以32,000元計薪聘僱,收20名司法兒少,需5位生輔員,政府補助每位生輔員薪資8,000元,機構每月得自籌12萬元的人事成本缺口;若想多請幾個人增加照顧能量,成本更高,造成生輔員薪資被壓低、也無法留才的惡性循環。 長期請不到生輔員,甚至有機構託少保官幫忙打聽哪裡有生輔員想跳槽。然而想成為生輔員,若非相關科系畢業,須自付25,000~26,000元修畢生活輔導人員專業訓練,才能取得資格。 「當父母有限制科系嗎?」有15年司法安置經驗的前高雄市私立康達家園主任黃月娥認為,不同科系畢業的生輔員,就像不同出生背景的父母,能豐富孩子的視野。她說,專業度應可透過職前訓練、在職進修精進。 也有機構指出,除了生輔員、社工,機構還要依人力比聘請心理輔導員、主任等。然而政府的人事補助金,得在機構收容率達5成的前提下,才有資格申請;這對立案時核定床位數較多,卻因請不到人、照顧資源有限而無法多收孩子的機構而言,成為一種變相懲罰。 雖然司法院從今(2018)年度起,將支應每名受安置兒少每月的安置輔導費用下限,從18,000元提高至21,000元,但這「下限」就和基本工資一樣,儼然變成各地方法院編列預算的天花板。而在實務上,照顧每位司法安置兒少的費用,每月至少花費3萬元。 |
|
2004-10
|
|
|
心情動態:
來自非公營房屋 |
「物價早就漲了,我們有時得跨縣市帶小孩出庭,這都需要成本,」徐瑜說,政府編列給公部門的少年之家(有提供少數床位供司法安置)的經費,每人每月補助4萬多元;同樣是司法安置孩子,有的有4萬元資源可用,但接公部門業務的民間機構萬一募不到錢,就只能用2萬1照顧孩子,為何公私立機構的資源分配如此不均?
徐瑜認為,政府既然規定機構的人力比,就應將這些人力的薪資全額補足:「你給我標配(標準配備),我自己擴充成全配(全套裝備)。你給我的錢能讓我專心顧孩子,若募到更多錢,我可以讓孩子過更好,不能老是『機構承接政府業務、還要募款補政府的不足』。」 照顧司法少年需要更高的成本,而目前對機構生存而言至關重要的評鑑,更難以反映接住司法少年機構的付出。 司法與社政安置,共用一份評鑑OK嗎? 衛福部每3年會進行「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聯合評鑑」,評鑑結果,會影響政府對機構補助款的比例,同時牽動社會觀感與募款能量。 本意是監督機構、提升機構照顧品質的評鑑,看在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CCSA)祕書長洪錦芳眼中,卻「是場災難」。 她認為,評鑑是對的,但評鑑是以人為主,還是以文書作業為主?評出來的結果,跟照顧孩子的品質是否對等? 洪錦芳指出,無論機構大小、收容兒少年齡、複雜程度,全都以同一份指標評鑑,欠缺公平。上百項的細瑣評分標準,讓工作人員被文書作業磨耗心神,無法將心力放在機構的照顧重點「孩子」身上,「最後機構就只收嬰兒、單純的社政安置乖小孩,最容易得優等。」 《報導者》訪問多間曾經或現正收容司法安置少年的機構,其實無人反對用評鑑來為機構素質把關,但對由誰來評、怎麼評,持不同看法。 黃月娥認為,3個小時的書面審核及現場訪視評鑑,所見有限,最好的評鑑方式,是讓評鑑委員來機構住3天:「我們耗費這麼多時間心力陪孩子,評鑑的主軸,不就該放在孩子的轉變上嗎?」 林劭宇表示,若評委不曾在機構工作,易產生理解與實務落差。他前份工作有協助毒癮少年,某次評委質疑,孩子反映3個月沒用手機很痛苦,有人權疑慮,「但他手機一打開都是藥頭的電話,能給他嗎?」 雖然社家署強調,機構收容非行少年等「特殊需求兒童」可列加分項目,「這只加0.5分!」林劭宇說,這些孩子不乏有過動、性侵、精神障礙與毒癮議題,這需要長期處遇,不會一進機構就變好。萬一評委不了解這段適應過程,質疑是否機構沒照顧孩子,孩子才會抽菸、打架、逃跑,0.5分沒拿到,前面分數都扣光。他開玩笑地說:「假如加20分,大家就會樂意收司法孩子了。」 林劭宇認為,照顧司法安置少年,確實要花較大能量,評鑑指標應分社政與司法類,並請有實務經驗的工作者加入評鑑,較能貼近機構現場的真實情況。 |
|
2004-10
|
|
|
心情動態:
來自非公營房屋 |
調整好再回家,或建立自己的家
雖然付出與回報未必成比例,但仍有第一線的實務工作者,在陪伴這群迷途孩子找路的過程中,找到使命與成就感。 康達家園由天主教聖功修女會在2001年成立,在2016年關閉前,是國內少數專收女少年的安置機構。相較血氣方剛少年,青少女之間的小團體與霸凌議題更加棘手。 前主任黃月娥笑著說:「女人比男人難搞。」她長年和自小走跳江湖的少年們混在一起,說話直爽,個性很man,一頭銀髮,別名「非行奶奶」。 康達家園共15床,起初只收社政安置的孩子,過程發現,許多社政孩子身上,往往會牽涉司法案件,例如逃家時餓到偷東西吃,因此康達逐漸開始收容司法安置少年。 「我們是政府說的替代式家庭、還是機構?說它是家,和孩子沒有血緣關係;說它是機構,大家又說希望像家,因為來到這裡的孩子,過往沒有家的支持,」黃月娥最後將康達定位為療癒型機構,給生命中遇到困難的孩子一個喘息之處,「等妳調整好,妳就離開,回到妳的家,或努力建構自己的家。」 既然定位為療癒,康達只收困難的個案,例如有自殘與攻擊傾向,或有精神醫療介入者。「太單純的我們沒辦法收,還曾因此被投訴。但我們的少女可都不是簡單人物,萬一來隻小綿羊,我們還要保護她!」 有多不簡單?「我第一天到康達,孩子跑來歡迎我,邀我去看她的房間。她房間木門凹一個洞,她把手伸過去,剛好卡進那個洞,『主任,這是我打的』。」 「下馬威耶!叫我第一天上班,罩子要放亮一點。」黃月娥瞪大眼。 「我們會幫孩子代存她們打工的錢,當時機構扣她5,000元說要換門,那孩子氣瘋了。我們知道她家境不好,等她結案當天,修女把那5,000元拿出來,加碼湊成一個紅包,當她的離別禮物。也讓她明白,我們不是要扣妳的錢,是給妳一個警惕,」黃月娥嘴角泛出笑意,「機構與孩子間的相處是很綿長的過程,萬一她到一半就逃跑了,就不知道我們在背後等她。這孩子常回來看我們,她現在在夜市賣鹹水雞,生意很好。」 療癒關鍵,是找到問題的痛點。康達開園不久,台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法官謝瑞龍與少年庭庭長、調查官一起到康達家園拜訪,請他們給國中少女「小宜」一個安置機會。 小宜父母離婚,父親不務正業,她自小在國學素養深厚的祖父薰陶下嫻熟繪畫、琴藝、書法。上國中後,卻因祖父母老邁無力管教開始曠課,騎贓車、逃家,還因竊盜等案四度被裁往觀護所收容,連母親都要法官乾脆送感化院。 謝瑞龍認為小宜很聰穎,只是需要一個暫時的家,連找5間安置機構,都以輔導困難為由不敢收容。黃月娥與工作人員評估3次,不忍小宜一再遭拒,內心創傷,同意安置。從小宜第一次進觀護所到被安置,前後歷時11個月。  少觀所中的觀護少女(非文中所指涉個案)。 |
|
2004-10
|
|
|
心情動態:
來自非公營房屋 |
回想小宜,黃月娥露出疼惜的笑容:「她很拗,情緒強度很高,跟工作人員衝突,就嗆『明天烤肉店見』。什麼意思?就她不爽要去死給你看,明天火化『烤肉』啊!她的心傷痕累累,心理諮商就做了58次。」
「她在康達2年,我們耗費1年半以上讓她穩下來。每次和工作人員衝突,她就說『叫我們阿龍來』,阿龍就是謝法官,」黃月娥不捨地說,「爸爸這角色在她生命中缺席,她一直在找個可以依附的父親,謝法官的真心相待,有讓她折服的地方。阿龍是個很親近的用詞,又想假裝她不在乎,每次謝法官來看她,她也不敢真叫他阿龍。」 小宜從機構結案後,順利國中畢業,在祖父資助下就讀感興趣的藝術學校。「幾年後,她抱著一個嬰兒來康達,原來結婚了,那是她第一個孩子。知道她怎麼跟她先生介紹我嗎?『這是南台灣最恐怖的歐巴桑,我做什麼都逃不過她法眼』;她還親自送油飯去給謝法官。」黃月娥笑瞇了眼。 康達開園之初,孩子的住所是原本的修女宿舍,後因對安置機構的建築規範逐年提高,宿舍多次整修,最終考量若要完全符合兒童福利設施規範,恐要耗費巨資重建,最終在2016年熄燈,回復為原本的修女修道院,原辦公室成為長照據點。 康達辦了為期半年的「結業式」,讓每個孩子規劃自己理想中的告別,辦了各種Hello Kitty趴、女王趴,讓這些過去一發脾氣就不告而別的孩子,學會好好說再見。 「康達熄燈,我有種夢未了的感覺,很多照顧孩子的經驗無法傳承,」目前擔任聖功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行政中心主任的黃月娥遺憾地說。 她認為,部分少年的非行原因,是因他們在原生家庭受到傷害,不解、矛盾、憤怒交織的情緒,讓他們自傷、傷人,或透過「犯法」向社會求助。安置輔導執行面有不少困難,但若能讓司法少年知道有人在他們人生的風暴中陪著吹風淋雨,就不用孤單地用賭一把的心態和風暴對衝,萬一挺不過,就成為社會的災難。 「我想,大家會留在這個工作,是因為司法少年能量很高。真正強悍的孩子,當他們找到自己的路,會用自己的雙手打拼,甚至不要我們提供的社會資源。若我們能提供適當處遇,改變他們,也就改變下一代與自己的未來。」 |
|
2004-10
|
|
|
心情動態:
來自非公營房屋 |
司法少年安置困境,司法與社福體系何解?
21年來「有法規裁定,沒機構執行」的司法安置困境,在Z機構事件後再度浮上檯面,社政與司法間如何解決?現在有幾派不同聲音。《報導者》採訪主責少年事件處理相關法規的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廳長謝靜慧,以及安置業務主管機關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兒少福利組副組長林資芮,了解兩大體系對於司法安置的立場。 ●「司法專門安置機構派」此派觀點認為,司法院應成立專門安置非行少年的機構,並有專責的司法社工。 →司法院持反對意見。 謝靜慧: 司法自己設安置機構,定位上會有問題。依照《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家庭失功能的孩子,需要一個替代性家庭,這是國家的責任,權屬機關也不該是法院。 司法少年所需求的社會福利,並非少年法庭本來就有的資源。安置業務的主管機關是衛福部社家署,若法院可以責付裁定或交付給行政機關執行,效能會比較高,也讓機構各有各的屬性與體質。 ●「公立安置機構擔起責任派」 國內5家公立安置機構,僅收容約1成司法少年。不少司法安置需求的孩子,同時被社政依高風險家庭等原因列管。此派觀點認為,全年預算由政府補足的公立安置機構,更該接起這些困難的司法少年。 →社家署持不同意見。 林資芮: 公立安置機構,是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成立並做社政安置,床位也有限。是因後來《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法,才配合做安置輔導處分。 兒少安置機構設置初衷,是照顧失去父母、遭虐待、須保護的孩子,人員的專業也以一般保護性兒少為主。觸法少年有行為矯正議題要處理,若與社政兒少共同安置,可能對保護性個案有一些不好的影響。 ●「修法取消派」此派觀點認為,既然執行上處處扞格,不如乾脆修法取消安置輔導處分,交回社政全權處裡。 →司法與社政雙方都不贊成取消,仍認為由回歸對方體系較妥當。 謝靜慧: 「但有需求的少年還在啊!拿掉一個法律名詞,這些少年誰接?」謝靜慧強調,當初有司法安置,是希望在司法保護處分中,有包含國家提供的替代式家庭司法處分。行政部門是否有能量提供符合司法安置需求的機構,才是要解決的問題。 林資芮: 社工人員不是矯正人員,更不是對司法兒少有強制性的執法人員。社政可給予社福支援,例如家庭扶助、心理諮商、團體輔導;家庭功能不健全的微罪少年,可裁定到機構安置輔導,若已需行為矯正,還是回歸司法體系較妥當。 然後呢? 部分機構與少保官認為,司法與社政系統之間,該要有個專責單位,擔任床位協調與安置業務聯繫橋梁。目前,社家署正計劃開放權限,讓法院能即時、透明地追蹤床位。 林資芮表示,今年6月起,若法院找不到床位,可找縣市政府社會局處的機構管理窗口,由窗口協助協調。另外,以往每3個月會彙整可供司法安置的床位給法院,未來將開通社政的「全國兒童少年安置及追蹤個案管理系統」權限,讓調保官可即時查詢各機構可收容的人數、性別、年齡、機構評鑑等第,讓資訊即時、透明,預計年底前可運作。 這帖解方固然踏出第一步,但問題根本的權責歸屬問題依舊無解。 「就算有床位系統,我們還是得一個個打電話確認,機構也還是能拒絕我們啊!」一名少保官說,「往好處想,Z機構事件真的有讓大家學到教訓。以前我找床位,打給機構劈頭就問:『你們有沒有空床?我有個孩子要評估……』現在是這樣問:『你們法定員額多少?實際負擔多少?現在收到幾個?我有個孩子要評估……』。」 |
|
2004-10
|
|
|
心情動態:
來自非公營房屋 |
「少年安置機構性侵案」彈劾風暴,法院和政府為何一再漏接?
 被勒令停收的Z機構收容宿舍空空蕩蕩。 被勒令停收的Z機構收容宿舍空空蕩蕩。[size=1.22222] 今(2018)年7月16日,監委無異議通過彈劾5名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處官員、3名地方法院少年保護官,創國內少保官遭彈劾首例;8月13日,監委召開記者會,說明已通過糾正南投縣政府、衛生福利部、法務部及彰化縣政府違失。不到一個月兩度糾舉、督促,是因為國內唯一純粹收容司法案件安置少年的「Z機構」,長期違法超收、被控暴力管教、3年來發生21起性侵案件。 為什麼15年來,法界會把孩子裁往Z機構安置?又為什麼這個彈劾讓司法界一片譁然?「司法少年」的安置出了狀況,孩子們能往哪去? 2016年底,15歲的A少年被學校老師發現罹患性病,進而追出他一年多前在南投縣Z機構安置時,遭其他院生性侵。2018年7月,我們來到因彈劾案再度成為風暴中心的Z機構。少年們的宿舍在3樓,窗外是炎夏藍天與連綿山景,空蕩蕩的房間各有桌椅與兩張上下舖,床板一塵不染,似乎有人整理過。鐵櫃半開,上頭貼著少年的姓名標籤,彷彿他們只是回去過暑假,開學就要回來。 白牆上貼著許多色彩繽紛的壁貼。這間機構在前年的機構評鑑中被評為丁等,評委的建議之一,是認為宿舍氣氛太冰冷,該有些溫度。機構負責人與被院生稱作「師母」的太太,遂買了壁貼給孩子裝飾房間。 這所立案19床、最高紀錄收容到106床的機構,曾收容台灣近半數的司法安置少年(每年約有250位司法少年 收容在安置機構);他們分別被安置在鎮上一處機構自購且立案的住所,以及4處租賃卻未立案之處。 2016年中,Z機構超收、院內性侵事件接連爆發,南投縣政府對這間機構進行超收列管,降低院內收容人數。到2017年6月,院內安置少年全數被少年保護官帶回,現在租賃的4處均已退租,只留下我們眼前這棟5層樓的立案處所。久無人居的宿舍,壁貼已失去黏性,一片樹屋已快從牆上掉下來,背景的星星顆顆脫落。 最後一個離開的少年 阿豪是這間機構最後一個離開的少年,他早在事發前就結案,自願繼續住在機構把高職念完。機構也轉請同宗教組織的基金會讓阿豪繼續免費居住,由南投縣政府社工定期追蹤。 |
|
2004-10
|
|
|
心情動態:
來自非公營房屋 |
受訪前幾天,阿豪才剛滿18歲,身材魁梧,一張圓臉仍帶稚氣。他父親是臨時工,跟小孩各過各的,阿豪國中開始結交幫派朋友,某次他兄弟挨打,他找來30人跟對方輸贏,吃下一條傷害罪,隨後又因偷竊被移送少年法庭,3年多前被法官裁定安置到Z機構。
他在我右邊坐下,背部向右斜靠著椅背,彷彿試圖再跟我們保持一點距離。 「一開始不適應機構,但跟著負責人和師母久了就會有規矩。我覺得這裡的生活很好,現在畢業了,每天自己起床,做完打掃就去上班,晚上回來洗完澡就睡覺。」 2017年3月,Z機構的院內性侵事件見諸媒體,監委主動申請調查,耗時年餘,發現機構不僅發生院內性侵,捲入其中的少年,還指控遭機構人員掌摑、打腳底等暴力管教,逃離機構被抓回,又慘遭痛毆,甚至打到牙齒斷裂。 問阿豪對這番指控有什麼想法,他停頓幾秒,「就是他們⋯⋯呃⋯⋯他們有的很皮,或不聽老師的勸告這樣。」 「那你覺得這種情況是?」 阿豪支吾,負責人接口:「管教。」阿豪鬆一口氣似地點頭:「對,管教。」 負責人與師母補充:「在《少事法》上,安置機構人員是少年替代性的父母,我們負擔他的權利義務,依《民法》也有懲戒權。但孩子怎麼看(懲戒權)這件事,有他們的角度。」 「以前還有法官託少保官拿棍子來給我們管孩子!」師母說。 「那你們有用這根棍子嗎?」 「當然沒有!」師母強調:「當然沒有!我只是告訴你,有時孩子去霸凌別人,把人打傷、牙打掉,打兩下手心不行嗎?這個管教是錯的嗎?」 最近縣府的社工向阿豪提供租屋補貼方案,為阿豪在鎮上找其他租屋處。但他不想搬,他說:「因為這邊生活比較規律,像個家,搬出去就沒有伴」。 問他有沒有話想對負責人夫妻說?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謝謝他們當時沒放棄我。」  曾被安置在Z機構,事發前已結案,不過選擇繼續居住的阿豪。(攝影/吳逸驊) |
|
2004-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