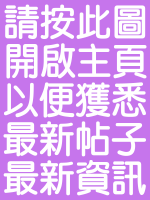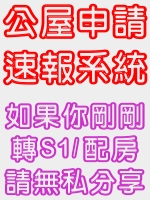|
心情動態:
來自非公營房屋 |
20年經驗護理師
20年經驗護理師:遺體護理,是你對另一個人能做的最親密的事
文:克里斯蒂・華特森(Christie Watson) 死亡永遠有兩種 [1] 希爾德嘉.佩普羅是一位多產作家,也是護理學家。她認為護病關係的最後階段(護理的核心意義所在)是解除和終止。護病關係唯有當病患出院或死亡才結束。「護病關係的一個關鍵面向就是護病關係是暫時的,跟社會關係相反。」佩普羅說。 她錯了。護理工作不是在輪完班就中止,也不是在病患死去之後就停頓。 一口白色的小棺材,另一個寶寶的葬禮。我跟同事在兒科加護病房照顧他六個月。薩姆爾是早產兒,肺部發育不全,需要多種呼吸輔助,因而引發了慢性肺病,肺部變得僵硬,難以輸氧且容易感染,一旦感染就嚴重到要接上維生機器。每到冬天,兒科加護病房就會人滿為患,擠滿像薩姆爾這樣好不容易撐過二十三、四週,卻不幸發育不良的早產兒。護理師瞭解家屬面對早產兒的心理煎熬:往往已經因為孩子早產而經歷無數心理創傷,一年後,在家受盡呵護的孩子又要回到醫院兒科加護病房,為生存奮戰。 薩姆爾母親的臉永遠痛苦得糾成一團,眼神溜溜轉,卻什麼也看不見。喪禮上來了很多人,傷心的家屬聚在一起,淚流滿面。我環顧教堂四周的哀悼者,大家都深愛薩姆爾。我數了數,包括我總共有六位護理師,其中三位輪完晚班後,坐兩小時的車趕來,已經二十一個小時沒闔眼。 護理師喬照顧薩姆爾的時間最久。喬是兒科加護病房的助理護理師。薩姆爾因為院內感染,需要隔離照顧,最後幾個月都是喬在陪伴他。喬一天有十二個半小時坐在薩姆爾和他母親身邊;晚上他母親到家屬休息室睡覺時,喬就獨自陪伴薩姆爾十二個半小時。我偶爾會去接替她,讓她歇一會兒,或是進去跟她確認藥物。她若不是在對薩姆爾唱歌,就是握著他的手,或是撫摸他的頭髮。薩姆爾的眼睛跟著她在病房裡轉來轉去,彷彿在對她笑,實際上他應該很痛苦。喬在口袋裡放著泡泡水,輕輕在他頭上吹泡泡,然後把泡泡一個一個戳破,直到薩姆爾開心地踢腿。醫生向他母親宣布噩耗時,喬陪在她身邊,即使已經下班,還是留下來把專業術語翻譯成簡單明瞭的話講給她聽。薩姆爾臨終之際,喬在他的手掌上塗了顏料,在卡片印下他的掌印,還從他後腦杓剪下一撮鬈髮給他母親。 這樣付出是一件危險的事,終究會承受不了悲傷,情緒崩潰。護理師承受的情緒太少獲得臨床上的督導,他們的所見所為也鮮少被探索,難以判斷他們的生活受到何種影響。然而,好的護理師為了幫助病患,甘冒危險。喪禮過程中,喬傷心得直不起身。後來,我看見薩姆爾的母親走向她,兩人在教堂裡抱著彼此,空氣中瀰漫的悲傷籠罩著她們身旁的小棺材。 護理助產協會職業規範明訂: 二十.六:隨時跟你照顧的人、他們的家屬和照顧者,保持客觀、清楚的專業界線(包括過去你曾經照顧的人)。 只是好的護理師不可能永遠客觀。喬是個優秀的護理師,她知道照護人就是去愛人,即使病患已經過世。 「遺體處理」也是護理師的工作之一。遺體護理,是你對另一個人能做的最親密的一件事。過程隱密,英國處理死亡的方式多半如此,而且也無法在教室真正學會。 我第一次看見屍體是在一般內科病房。當時我被分發到那裡受訓。跟我共事的護理師都是菸槍(有個懷孕肚子很大了,仍要出去哈菸),身上戴了太多首飾,頭上頂著失敗的髮型。這裡的病人罹患各式各樣的內科疾病,如糖尿病、失智症、心臟衰竭、慢性肺病、腿潰瘍、髖骨斷裂,需要有人幫助他們飲食及如廁。工作項目重複性高。我們一一幫病患洗澡,不是看誰比較急著用便器,而是按照床號。一號床病患第一個洗,就算病患在睡覺也會被叫醒。 但今天什麼都往後延。病患在床上坐起來,因為不用被迫坐上椅子或在病房裡走來走去而一臉欣喜。 |
|
2004-10
|
|
|
心情動態:
來自非公營房屋 |
我走進病房時,有兩名護理師正在按摩一名死去病患的關節。我推著茶具走進去,推車搖搖晃晃,鏗鏘作響。我停下腳步瞪大雙眼,不自覺地張大嘴巴,直到名叫凱莉的護理師抬頭對我說:「親愛的,不要緊。他命很好,走得很安詳。家屬都來了。」
「對不起,」我說,拉著推車往後退。「我從沒看過。」 我慢慢後退,每退一步都差點彎腰鞠躬,總覺得有莊重肅穆的必要。我發現兩名護理師都在按摩他的手腳,好像他還活著似的,儘管他顯然走了。他的皮膚已經灰了,嘴巴開開的,看起來不像人。 「把推車擱在外面,來幫我們的忙。」凱莉說。 我想拒絕,找個藉口溜走,再也不要看見發灰的屍體,但我知道我要堅強。 我在門外先深呼吸再走進去,穿上圍裙,把推車留在外面。「妳可以從手肘開始。」凱莉說:「已經出現屍僵現象,但我們可以按摩讓它退掉。」 我有點噁心,猛吞口水,盡量不把眼前的男人想成一個人。這是我唯一能面對的方式:只想著他的手肘(現在變成味噌湯的顏色),輕輕按摩它,讓它不那麼僵硬:不那麼死板板。我盡量不去看他兒女的照片。還是孫子孫女?曾孫? 後來凱莉跟我解釋我們正在做的事:按摩出現屍僵現象的肌肉,再用枕頭撐起他的手臂。「這樣他的手臂才不會失去血色或長出屍斑。」她說:「沒有什麼比屍斑更讓家屬傷心的。然後我們把他的假牙裝回去,用枕頭撐住他的下巴,接著為他擦洗。稍微打扮一下。最後幫他貼上標籤,再用床單包起來。夏天就得這樣做。要是蒼蠅飛進鼻孔或嘴巴,遺體很快就會長蛆。再沒有什麼比這對家屬打擊更大。」 我目不轉睛盯著另一個懷孕的護理師。她喃喃說著:「是壽衣,不是床單。」我不敢問什麼是屍斑,努力想要趕走腦中屍體長蛆、自己死後蒼蠅鑽進體內、身體變得怵目驚心的畫面。 那天下午大概四點時,我趁著吃午餐到外面去走走。 「在想什麼?」跟我坐在同張公園長椅上的男人問我。 「生命與命運。」我說。 他哈哈笑。「聽起來好嚴肅。」他轉頭面對太陽,閉上眼睛。「多美好的一天。」 我旁邊是助理護理師莎薇。我們正在處理一個在祖父母家中池塘溺斃的六歲女童遺體。房間裡好亮,我們已經盡力拉上每扇窗戶的百葉窗。 房間沐浴在深黃色的光線中。躺在中間的女孩名叫芙蕾雅,在床上顯得好瘦小,頭仍躺在枕頭上,我們想盡辦法還是沒能讓她的眼睛完全闔上。我一直用指尖輕輕按住她的眼皮,為她闔上雙眼,但眼睛照樣彈開,彷彿從噩夢中驚醒。死者的父母、祖父母和兩個兄姊(分別是八歲和十歲)決定不進來看我們進行的最後儀式。他們在病房入口旁的家屬休息室等候,我盡量不去想像他們在那個房間的情景:他們無法對彼此說的話,尤其是祖父母內心的自責。每個死亡都是一齣小悲劇,但芙蕾雅的死很殘酷。 她接了導尿管、氣管插管、中心靜脈導管、兩條周邊導管,還有兩支骨間針插在她的骨頭裡,此外,還有胸管和鼻胃管。「我們不可能把所有東西都拔出來。」我對莎薇說:「應該把東西都留在裡面,用塞子封住,再包起來。我會從她口中剪斷氣管插管,然後包住,這樣看起來就不會太糟。對家屬來說,這當然很難受。」 莎薇站在我後方,大房間裡已經沒有機器了,病床旁邊很空。「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屍體。」她說。 我深呼吸。我老是忘了這件事。年紀大了,從事護理工作多年,離年輕時的自己和豐沛的情感愈來愈遠,我納悶自己是不是還有那種感受。除了家屬,醫院裡總有其他人為病患的死深受震撼:醫生、護理師、每天帶茶和點心來跟病患聊天的志工、協助病人看菜單的醫護助理、走進病房的理髮師、來檢查藥單順便小聊一下的藥局助理。但感受最強烈的往往是助理護理師。資深護理師已經想辦法把心變成冰塊,以保護自己,但是要讓心變硬,得經過多年練習。我數不清自己看過多少遺體,太多了。護理師很多時間都跟垂死的(昏昏沉沉、口齒不清)病患在一起,還有斷氣不久、還沒送進太平間、肺部仍有空氣的病患,病房裡仍充斥他們睡衣的氣味,彷彿聽得見他們的聲音。他們的微粒飄浮在空中,化為光線裡的灰塵。 |
|
2004-10
|
|
|
心情動態:
來自非公營房屋 |
「有時候說話會有幫助。我是說大聲說出來,」我對莎薇說:「當作這孩子還在這裡。」
莎薇從我後面走出來,淚水滿面。「可憐的一家人。」她說。 我搭著她的肩膀,輕輕抱住她。「哭沒關係的,其實哭很好,讓家屬知道妳真的在意。」我命令自己流眼淚,但淚水埋得太深。「哭吧。」我對自己乾巴巴的眼睛說:「哭吧!」 「在我的文化裡,為死者哭泣的時間是有限的。印度教認為應該為死者服十三天的喪。而且幫死者淨身的是家人,不是護理師。」 「這裡有時候也是。」我說:「但不是每次。最好問清楚,尊重家屬的意願。芙蕾雅的父母受到的打擊太大,連站起來都有困難……」我看著芙蕾雅。她的身體腫脹瘀青,皮膚發灰,被各種儀器覆蓋。「開始吧。」我對莎薇說,然後轉向芙蕾雅:「小可愛,我們要幫妳小小梳洗一下。」 我跟很多同事一樣,都會跟死者說話。這樣死者就不那麼像真的死去,護理師才能做好該做的工作,不至於傷心崩潰,或是感覺到死亡嚴酷的威脅。對死者說話,讓人感覺他們還活著。人死去後,房裡會有一種氣息。若你有經驗就會知道,就像跟人爭辯之後、還有什麼飄浮在空中的感覺。我認識的護理師多半都很務實,相信遺體就只是遺體而已。而我們不過是在空中飛舞的塵埃。不過每個護理師當然都有自己的鬼故事。 「妳去把水裝滿,我把東西拿出來。」 莎薇盛了一盆溫水。 「熱一點。」我說:「這樣她父母進來時,芙蕾雅的身體才不會太冰。」 莎薇抽抽鼻子,別過頭。 「慢慢來。」我又說。我的臉好乾,甚至有點癢。 我用酒精棉片擦拭塑膠托盤——習慣比什麼都要重要。芙蕾雅現在不會再發炎或感染了,但習慣讓一切如常,彷彿我正在觸碰一個活著的病童身上的中心靜脈導管。她沒有流血,但體液從邊緣組織滲透出來。我用紗布盡可能把滲透處蓋住。我拆下膠帶,在她的皮膚和導管上放上乾淨的繃帶。她的手臂下也滲出體液。我移動她的手臂,慢慢按摩,希望等一下她父母進來時,看起來會比較正常。現在我知道什麼是「屍斑」了。再清楚不過。「血液沉積」之類的神祕字彙對我再也不陌生。 莎薇開始清洗芙蕾雅的皮膚,動作緩慢而輕柔,嘴裡哼著歌。從頭到腳幫芙蕾雅梳洗時,她把手放在芙蕾雅的胸前。「引領我們從蒙昧走向真理,」她說:「從黑暗走向光明。」 「妳看起來好多了。」我對芙蕾雅說,她的眼睛終於闔上。清潔之後,莎薇在她身上塗了嬰兒乳液,讓她的皮膚閃閃發光,還幫她換上了睡衣。少了管子,芙蕾雅看起來不像死去,更像是睡著了。「最後一件事。」我說,從床頭櫃裡摸出一支有粉紅恐龍造型頭蓋的小牙刷。我打開蓋子,擠了一點芙蕾雅的泡泡糖口味牙膏在牙刷上,然後刷一刷她方方正正、潔白無瑕的小牙齒,直到鼻腔裡都是泡泡糖的味道。 醫院的員工就是他們服務的病人的寫照。護理師、醫生、搬運工、醫護助理、廚房人員、清潔工和技術人員,全都來自世界各地,各種你想得到的背景、種族、文化和宗教都有。跟我共事過的護理師,有無神論者、佛教徒、福音派教徒、伊斯蘭教徒、錫克教徒和天主教徒,也有修女,有些人信奉的宗教我聽都沒聽過。「我相信水晶療法和天使。」有個同事曾告訴我。還有另一個同事說:「我信仰伏特加。」無論他們信仰什麼,信仰多麼低調或隨性,當病人死去時,護理師的個人信仰就變得很重要。 |
|
2004-10
|
|
|
心情動態:
來自非公營房屋 |
基督教從一開始就鼓勵信徒照顧病人。其實從古早時代起,很多文化都培養了為宗教獻身的護理師。現今很多護理師沒有信仰,或是擁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心靈依靠,但尊重差異是護理師的責任。最好的護理師把每個病患都當作親人或心愛的人,而照顧臨終病患,讓護理工作呈現最有創造力的一面。心靈的語言,其實就是把神祕難解的事化為文字的一種方式。每個家庭或許都有自己習慣的宗教儀式,但尊重個別差異才是「人類一家」的真正內涵。護理師必須尊重病患的心靈,無論表達方式為何,有時甚至因此要壓抑自己的信仰。舉例來說,曾經有護理師因為替病患禱告而被開除,因為醫院明訂護理師有責任照顧病患,但不能主動提供對自身信仰的看法。我曾經跟一些護理師一起工作,他們認為隱藏自己對上帝的信仰,比假裝自己是會飛的大象還難。那是他們的自我認同,是他們之所以成為護理師的初衷。 我跟所有護理師一樣,學會了各種信仰的應用知識——跟生死病痛相關的知識。但課堂不是你可以學會照顧人類心靈的地方。我對伊斯蘭的瞭解不是從護理課本學來的,而是從一位信仰伊斯蘭的病患及其家屬。死前,他要求我把他的頭轉向右邊,面向麥加。來看他的人絡繹不絕,他雖然痛苦,看到親友還是很開心。我發現他的家人信任神的旨意,更勝醫生說的話。無論是何種信仰,終止照護永遠是最困難的一個題目。 耶和華見證人這個宗教給我的震撼教育尤其大。有個年輕母親在急診室裡流血過多而死,她拒絕了能救她性命的血液。因為她的信仰,我們只能眼睜睜看著她死去。護理師對病患信仰的尊重,有時表示我們只能任憑病患死去。照顧病人是一項愈來愈全面的工作(也應該如此),但有時照顧病人的心靈,表示只能放棄他們的肉體 |
|
2004-10
|
|
|
心情動態:
來自非公營房屋 |
我女兒五個月大時,我回到兒科加護病房工作。托兒所八點一開,她父親就會把她送去(我六點半就要出門),晚上六點我再去接她。丟下她去工作,讓我每天晚上都一身冷汗醒來,滿心愧疚,但是當媽媽讓我變成不一樣的護理師。我開始注意到小地方大不同。對我來說,喪親扶助護理師一向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突然間我發現她不可或缺。我對她的敬意難以用語言形容。她自己也有小孩,卻花很多時間幫助失去小孩或正在面臨死別的家庭。她也幫助醫院的員工,從莎薇這樣管不住情緒的助理護理師,到已經封閉情緒的醫生都有。她是一流的翻譯員:「醫生是說,我們已經幫不了莎拉。但他真正要表達的是,我們救不回你孩子的身體,他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我們都是。不過,還是有我們可以做的事。為了莎拉,也為了你們。我會在這裡陪你們,接下來幾天,讓我們一起製造美好的回憶,確保莎拉不再痛苦,走得平靜又安詳。你們可以抱著她,陪在她身旁直到她離開。我會在這裡,陪在你們身邊。」 太平間是我們所有人最後的歸宿,卻是大多數人難以想像的地方。第一次走進太平間時,我屏住呼吸,穿過一扇又一扇的門,最後站在一層層白色冰櫃前。白色日光燈、白色冰櫃和白色牆壁,裡頭的一切看起來都冷冰冰又不真實。太過嚴酷。跟自然相反。毫無一絲味道,沒有平常瀰漫醫院的各種味道,如漂白水、汗水、血液、茉莉花、尿液、鬍後水、薰衣草護手霜、薄荷糖、髒頭髮的菸味、消毒酒精、糞便。 裡頭什麼味道也沒有,是你想像得到最不陰森的地方。如果世上有鬼,也不會在太平間。這裡毫無生命可言。什麼也沒有。「前一秒我們還站在這裡,」第一次走進太平間時,有個技術員聳聳肩說:「下一秒就沒了。」 病患被送到太平間的過程因醫院而異,但大致如下:搬運工會先把遺體搬到推車上(如果無法直接滑到車上的話),再貼上標籤並建檔,然後關上冰櫃。肥胖的病患有特殊的冰櫃(愈來愈常碰到),就像冰庫一樣,可以走進去,不需另外搬運。嬰兒的冰櫃較小,通常由護理師或助產士把他們帶過來。胎兒若未超過二十四週,就不會登記死亡。「連死亡證明都沒有,要我們怎麼哀悼?」 我對這些事已經不再敏感,對生死和生死之間的一切也早已習慣。但是我很難形容(或是忘記)從太平間冰櫃裡拉出來的遺體的冰冷皮膚。死亡跟生命一樣有著不同的階段。往往當家屬前來弔唁、遺體準備下葬或火化,或是醫院需要驗屍(常有的事),必須把遺體從冰櫃拉出來時,眼前所見跟原本活著的人已經判若兩人。臉和膚色都變了,身體也變得更小、更白。 然而,太平間也讓我近距離目睹了無畏的愛。有個禮拜我苦不堪言,擔心公立醫院護理師的薪水太少,沒錢繳快到期的帳單,再加上車子發動不了,家裡又有感冒喉嚨痛的小孩,一個送去托兒所,一個送去學校。我餵他們吃了退燒消炎藥,心裡隨時準備接到老師的電話,要我把他們帶回家——這對忙得團團轉的護理長是不可能的事。 輪班到一半時,我陪一個母親去看她死去的兒子。我記得當我們走進查克瑞停置的房間時,她在我身旁渾身發抖。查克瑞包著柔軟的毯子,放在推車上的箱子裡。記得我當時心想,自己的煩惱相較之下,顯得多麼微小和自私。那房間很狹小,隔壁就是太平間。她靠上前,對兒子輕聲說著一些我聽不見的話。我盡可能站遠一些,怕打擾到這樣的私密時刻。但之後她後退幾步,把我拉到身旁,抓著我的手。她沒哭,只是看著他,用大拇指觸摸他的輪廓。查克瑞看起來更小了,原本溫暖黝黑的皮膚失去了光澤。我對他很熟悉,因為已經照顧他好幾個月,最後幾天都在準備他臨終的事。我們跟喪親扶助護理師一起在他臨終之際剪下他的一撮頭髮,把他的腳丫塗上金色。我幫他蓋了腳印,幫他們母子拍照,全天播放他最愛的音樂。 |
|
2004-10
|
|
|
心情動態:
來自非公營房屋 |
|
|
2004-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