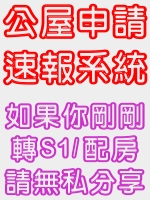|
心情動態: 來自彩盈邨 |
尋找一九四九龍應台苦澀之旅 .張潔平
龍應台從家族史出發,寫出人性化的一九四九,「向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致敬」。她持續三百八十天的歷史之旅,往南京、廣州、長春、瀋陽、馬祖、台東、屏東、美國等地訪問親歷者、查考歷史現場,還有五六十人的口述回憶,寫成《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發現「所有的顛沛流離,最後都由大江走向大海,所有的生離死別,都發生在某一個碼頭 —— 上了船,就是一生」。她在寫書時沒掉淚,卻在受訪時感動落淚。 與很多人不同,龍應台關於「一九四九」的寫作,是在周圍人的注目禮中開始、進行和完成的。 這個四九年後出生在台灣的國軍後裔、眷村女兒,二零零八年開始,「入駐」在香港大學為她專設的「龍應台寫作室」。她向自己的學生徵集父母一輩的口述歷史,向全社會尋找一九四九的民間記憶,飛往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查閱蔣介石日記,往南京、廣州、長春、瀋陽、馬祖、台東、屏東等地訪問親歷者、查考歷史現場;一路都向四周的新朋舊友不厭其煩地打聽他或她的祖宗家事、家族遷居史。塵封多年的私人日記、歷史照片,還有五六十人珍貴的口述回憶,在這個執著的詢問者面前一一打開。 最後,帶著這一切的體溫、感傷、痛苦以及盼望,她在台北金華街的辦公室熬了三個月,在浩如煙海的檔案材料與口述錄音中把自己浸透又抽離,一字一句,寫下十五萬字「龍應台眼中的一九四九」。 她給新書起名:《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二零零九年九月二日,《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在台灣正式面世。九月九日,有關本書的媒體茶聚會在香港召開。香港各大書店裏,《大江大海》放在最顯眼的位置,平均一兩個小時就要增加一,不少中國大陸訪港旅客帶幾本回去,當做「國慶六十週年」的別樣紀念。 身為失敗者下一代為榮 短短一個多星期,龍應台已經收到數不清的讀者來信,許多是年輕人,幾乎所有人都說,是流著淚讀完這本書。 對龍應台自己,這是從未有過的寫作體驗。持續三百八十天的歷史苦旅,她嘗試找回父親母親所經歷的真實的一九四九,也找回許許多多普通人的記憶。在那一個年頭,倉皇奔逃或者倒下的普通人,看不到大時代的風雲變幻,也看不到江山易幟的激動人心,他們的個體命運,只是承受著太多流離,太多夢碎,太多被碾碎的青春和被奪走的生命。如作者在短介中所寫:「所有的顛沛流離,最後都由大江走向大海,所有的生離死別,都發生在某一個碼頭——上了船,就是一生。」 書的扉頁上,龍應台寫著:「向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致敬」;她寫:「我,以身為『失敗者』的下一代為榮」。 套用龍式文法,這可能是一個「你所不知道的一九四九」。無論在台灣、香港、中國大陸,或是任何一個華人社會,書中描述的一切,都會讓你感到陌生——而這種陌生,正是寫作本書的過程裏,作者發現的另一個驚人事實——短短六十年光陰,竟在各地,以各種理由,製造了數不清的記憶「黑匣子」,以至對於並不遙遠的一九四九,我們甚至無從「回憶」,只能「尋找」。 緣起,是龍槐生和應美君的故事。 在作者介紹裏,她這樣寫自己:「『龍應台』不是筆名,是真名;父親姓龍,母親姓應,她是離亂中第一個出生在台灣的孩子。」 應美君懷裏抱著剛生的孩子「應達」,一九五零年從海南登上開往台灣的大船。台灣——在哪裏?是什麼地方?誰也不知道。生長在浙江淳安的美君不知道,生長在湖南衡山的丈夫——國府駐常州的憲兵隊長龍槐生也不知道。 在一九四九年一批一批撤退往台灣的國軍艦船上,甚至有駕船的海軍逃開砲火射程,才拿出地圖來找台灣的位置:「聽說那地方叫『台灣』,我也沒去過,你也沒去過,聽說那地方不錯。」 |
||
|
|
|||
|
心情動態: 來自彩盈邨 |
美君和槐生在台灣高雄的碼頭找到了彼此,他們,和一批一批,流落在這陌生港口的前後一百二十萬國軍士兵、家眷一樣,滿懷忐忑地打量這個陌生的小島。
一九四九年離開家鄉時,他們都沒有回頭,年輕人都以為,那不過是暫別。誰也沒想到,一上船,就是一輩子。 在高雄出生的龍應台仍然記得,年少時候,父親總是拿出一雙蒼黃的布鞋底,在兒女面前講起往事,泣不成聲。因為往事說得太多,戰亂後長大的少年厭煩了,邊聽邊嘲笑,聽完便算,也不深究。 那雙鞋底,正是一九四九年,祖母在衡山老家與父親匆匆作別的一刻,塞進父親懷裏的。那一刻,竟是最後一面。只是這個故事,小女兒應台再沒有機會聽完整。 在書裏,龍應台寫:「那麼多年的歲月裏,他多少次啊,試著告訴我們他有一個看不見但是隱隱作痛的傷口,但是我們一次機會都沒有給過他,徹底地,一次都沒有給過。」槐生逝世五年之後,美君亦已失憶,連最愛的女兒也喚不出名字。 龍應台終於完成了關於一九四九的寫作,觸到了父母那一輩人曾經歷的真實傷痛。可惜「最大的遺憾,父親看不到了,母親看不懂了。這本書是寫給他們的。」 緣起,是要追問父母未盡的言語,追尋自己從何處而來;結果,揭開了整整一代人「隱忍不言的傷」。 回憶起一九四九,海峽兩邊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台灣人說「民國三十八年,兩百萬國軍撤退到台灣。」中國大陸,講「國慶六十週年」、「建國六十週年」。兩種理解,都讓龍應台覺得不能接受。 「你要知道,這兩百萬人,不是『砰』一下子,就來到這島上的。」 「寫書時,人家說龍應台在寫一九四九,我周邊在香港的人,第一反應會是『哦,建國六十年』。這給我蠻大一個震撼:整個中國大陸的十三億人,其實完全不知道,這些被國共戰爭的機器絞出來的人的命運,他們後代的命運。要講兩岸如何如何,其實連基礎都沒有。這個台灣,你完全不知道是什麼樣的人到了那兒,然後帶著什麼樣的傷感,什麼樣的創痛。」 香港大學柏立基學院的龍應台寫作室,背後是山,窗外面海。書桌堆滿檔案,後邊豎著白板架,上面塗畫寫作過程裏每一個階段的構思與關聯;前方,則是一整面牆的中國地圖,圓點標記出龍應台一路計劃探訪和已經探訪的地方。 孤軍被關在越南集中營 「你看,這些人,是被絞肉機一樣,從這個國家一股一股絞出來的。」龍應台指著地圖上的中國大陸,手指向四面拂過,「在最開始的時候,我想寫的是從那個機器被絞出來的六、七股人,你知道嗎?甚至有一小股國軍孤軍是從甘肅、青海直接逼進印度和巴基斯坦,那是不得了的故事,也有上千人;在西南,從雲南進入滇緬是一股,是第二股了;第三股到越南,第四股到澳門,第五股到香港,第六股到台灣,第七股是沿海,從舟山群島一路下來到金門、馬祖、烏丘、江浙跟福建。」 每一股,都有悲傷的故事,由廣西進入越南的一支,在法屬越南的集中營被關三年半,生命一半一半地消亡,倖存者一九五三年才回到台灣。到澳門也有一支,龍應台說,各種資料顯示有國軍孤軍到了澳門,但他們未來如何,是死是活,所有的資料都沒有詳細記載,所有相關機構都不知道,「真的像輕煙一樣」。 一九四八年,詩人弦還是河南南陽的一名中學生,十六歲。他和五千個南陽中學生一起,躲著內戰的硝煙大撤退。一路步行到湖南,遇上振奮人心的招兵廣告「有志氣、有血性的青年到台灣去」,他們很懂飢餓少年的心思,還送上一大鍋熱騰騰的紅燒肉。少年弦於是滿腔熱血地加入,到了台灣。再回家,已是四十二年之後。此間,父母音訊全無,何時過世,如何過世,全不知情。母親一起做針線活的朋友輾轉傳了口信:「我是想我兒子想死的,我兒子回來你告訴他,我是想他想死的!」 六十年後,弦向龍應台說起這段往事,眼淚簌簌流個不停。 還有許多十八歲。龍槐生十八歲,遇上一九三七年南京保衛戰,成了國軍的愛國青年。台灣卑南族青年陳清山和吳阿吉十八歲,遇上一九四五年國軍在台灣徵兵,當時只說招工,兩個窮小子於是到了大陸,當國軍,被俘虜了,又當解放軍,從此在大陸生活五十年。李維恂十八歲,正是抗戰,愛國、從軍,在日軍統治的上海,做游擊隊長,進行敵後爆破。一次行動中被捕,被送到南京老虎橋集中營,一九四三年,和一千五百多名國軍俘虜一起被送上船,到幾千里以外的新幾內亞拉包爾島,關進那裏的集中營。 拉包爾倖存者等待這天 六十年後,接到龍應台要尋找拉包爾集中營倖存者的信息,八十九歲老人說的第一句話是:「我知道為什麼我的戰友都死在拉包爾,但我李維恂獨獨活到今天。我在等今天這個電話。」 還有多少十八歲,變成殘破的屍體,倒在熟悉的土地、陌生的戰場上?還有多少母親,永遠等不到回家的孩子?多少姑娘,永遠等不回不告而別的戀人? 一場戰爭,究竟誰是勝利者?還是如龍應台所說:「請凝視我的眼睛,誠實地告訴我:戰爭,有『勝利者』嗎?」 龍應台說:「北京剛好在慶祝建國六十年,還有很多論述會講:『在東北遼瀋戰役中十二天殲滅四十七萬人,在徐蚌會戰(即淮海戰役)裏五十天殲滅五十五萬人』,現在還在講軍事史,我看到心裏蠻痛的。你究竟知不知道,你所殲滅的那些人,都是東北和山東的子弟,十八歲的人,你一定知道的。但為什麼過了六十年,還在用這種語氣去談呢?過了六十年,是不是該有一個新的態度,尤其是勝利那一方,可以有一個更貼近人性、更關懷、更謙卑的態度來看這個問題?」 歷史在兩邊,都留下了太多黑盒子。 長春圍城歷史被湮沒 在走近一九四九之前,龍應台花了百分之八十的時間大量閱讀資料。她說:「在出發之前,我帶著一個巨大的好奇,想要知道我們這一整代人對一九四九已經有的支離破碎的認識。我想要看歷史根據,去知道,我們原來有的那種認識到底是不是真的。」 即便如此,重重迷霧仍讓她訝異:在大陸,一九四八年的長春圍城,整整五個月,飢殍遍野,餓死的人數統計從十五萬到六十五萬,慘烈程度不亞於南京大屠殺。後來,「勝利」走進新中國歷史教科書,長春被稱為「兵不血刃」光榮解放。六十年過去,龍應台去採訪,這城市來來往往的路人,竟無人知曉曾有數十萬人餓死在這裏! 在台灣,一九四九年國軍從廣州碼頭撤退到台,甚至連哪一個碼頭,國軍檔案都沒有留下記錄。不要說那許多流落各地的孤軍,更不要說日據時代曾被徵召入日軍上中國戰場的台灣「軍伕」。「台灣的歷史教科書,從一九四五年,砰一下就跳到一九四九年,然後就是五十年代的台灣。」龍應台說,「那個戰敗心理,到現在還是無法面對。」 一邊,是戰勝者的洗刷,以權力重寫歷史;另一邊,是戰敗者的隱筆,對恥辱選擇性失憶。六十年光陰,親歷者蒼老、死去,滄海桑田無聲無息,一九四九,最後剩下的,只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乾淨。 後來者無從回憶,無處尋找,連六十年後,要重新進入那情境,都變成難上加難。 八月四日,龍應台交了《一九四九》的初稿。八月八日晚上,台北的朋友開了慶祝會歡迎她「出獄」。在慶祝會上,龍應台聽十二個好朋友議論剛剛完成的書稿,心裏一驚。第二天,她執意把已經排版了一半的稿子拿回來,全部打碎重寫。整整三十六個小時,沒有睡覺,把章節次序全部調整。原先的第一章,變成第五章,美君與槐生的故事,這才成了最開篇。 |
|
|
|
|
心情動態: 來自彩盈邨 |
曾經打碎重寫調整章節
龍應台發現,原來人們對這段歷史太陌生,講東北聯軍、解放軍,看來很常識的歷史,許多人完全進不去。「沒有概念到一個程度,原來的第一部完全進不去, 尤其年輕人進不去。年輕一點的小朋友,(國軍將領)黃百韜也沒聽說過,孫立人也不知道。國共內戰,什麼跟什麼都不知道,那我才想說,那要比我的預期還要再降低點,門檻要更低一點,要更溫柔地帶他進入。」 「從家族史到國族史」,「下歷史的功夫進去,乘著文學的翅膀出來」,這是龍應台對自己這厚厚三百多頁書卷的定位。所有材料都來自真實史料或第一手的訪問材料,長達一百二十七項細緻的註解可以證明,落在紙面,化作一張一張普通人的鮮活臉孔,他們真切的苦痛與哀傷。 最令作者震撼和難忘的,是那些被隱藏更深的一九四五年以前的台灣故事。 「開始,我想了解一九四九年那兩百萬突然來到台灣的外省人怎麼回事。但是我很快發現,要真正了解那個時代,怎麼可能不問另一個問題:這個島上一九四九年原來就有六百萬人,這六百萬人在四九年前過怎樣的生活?他被教了好幾代,是日本人,讀日本書,聽日本音樂,欣賞日本文學。突然,一九四九年來了兩百萬人。難道他們沒有想法嗎?難道這衝擊不大嗎?我才發現,原來我對他們的了解等於零。從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九,我只知道一件事情: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四年歷史被一個『二二八』所壟斷,這合理嗎?」 巨大的問號帶著龍應台回頭去找那六百萬在地的台灣人,他們是怎麼走過來的。「這是完全不同的語言、文化、歷史脈絡,而且痛在完全相反的地方。中日戰爭的時候,他們是在日本一方的。那麼他們之間的碰撞到底是怎麼回事,而且那種碰撞,其實就一路走到六十年後今天的台灣政治,藍的或者綠的,本省的或外省的。」「原來,要了解一九四九,我一定要回到一九四五。」 中日戰爭時候的台灣,如今已無法言說。你怎麼理解,日本在台灣招一千名軍人,結果有四十萬個台灣年輕人應徵?這些少年,被選上曾是鄉里的榮耀。龍應台說:「當時六百萬台灣人,有二十萬子弟被日軍送到南洋、海南島、新幾內亞去,死了三萬三百零四個人,活著的人回來發現,從此以後你的孩子以你為恥。」 台灣作家黃春明訴說自己的故事,他很記得一九四五年,宣布天皇戰敗那一天,在學校裏聽到了廣播,他回家,看到爸爸傷心得不得了,說台灣淪陷了、戰敗了;爺爺卻高興得不得了:解放了。 「那是一九四五年,台灣人處於一個完全沒有辦法處理自己的錯亂的處境裏,他們都是失敗者。後來,兩百萬失敗者又來到島上,帶著完全不同的創傷。他們被不同的國家機器控制、塑造、傷害、踐踏,而失敗了到這裏來。也正是因為這樣,這六百萬加兩百萬的失敗者,在之後六十年裏頭,創造出一個不同的社會,奠定了不同於以往的價值。」 龍應台本想將書獻給所有「失敗者」,可最後,她還是改成:獻給「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 「這是一本很悲傷的書。」書稿已經付印,龍應台仍然不怎麼會笑。「我有時想到當年在瀋陽火車站前面自殺的那個國軍軍官,他在地上用白色粉筆寫著:『我是軍校十七期畢業生,祖籍湖南』,我父親就是湖南人,軍校十八期……這本書裏,有三千萬亡魂,太多亡魂了……」 寫作過程裏,她恪守創作者的原則,從未掉過一滴眼淚。此時,卻哽咽起來。在後記裏,她說自己在做一件超過自己能力的事情,「但這件事情所承載的歷史重量,觸及了我們心中最柔軟,最脆弱的地方」,她說要「不離不棄」。 輕輕抹去淚水的龍應台,輕輕說了一句話:「我想要透過這本書,讓那許多許多的亡魂,在這六十年後,在詩的意義上,入土為安。 」■ (亞洲週刊實習生周續娟、王點點協助採訪) |
|
|
|